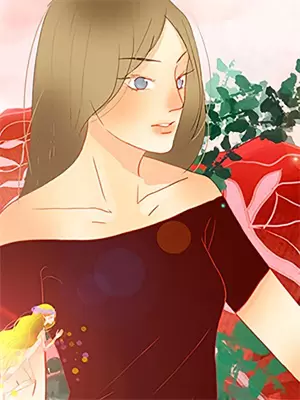1 占卜六月的风已经带上了暑气,黏糊糊地扑在窗玻璃上。吴娟揉了揉发涩的眼睛,
视线从摊开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笔记上移开,落在窗外。琳琳的房间门关着,
里面静悄悄的,大概还在刷题。中考志愿填报像一块巨石压在这个家的屋顶,
也压在吴娟心口。每一个选项都重若千钧,关乎女儿的未来。她需要和周涛商量,
哪怕只是听听他的意见,哪怕他依旧只会说“你看着办”。她拿起手机,
屏幕上是与周涛的聊天界面。最后几条消息停留在她这里,绿色的气泡,孤零零的。
“琳琳一模成绩下来了,还不错,就是数学有点悬,选学校得慎重。
” “志愿表发你邮箱了,有空看看。” “打电话怎么不接?在忙?” …… 石沉大海。
上一次通话是什么时候?三天前?她好不容易打通,背景音嘈杂,他语气极冲,
像是她打扰了什么天大的正事。 “又怎么了?天天就知道孩子孩子!我在外面拼死拼活,
血压都上来了,你关心过一句吗?我这命都快搭进去了,不就是为你们娘俩?” 声音很大,
震得她耳膜嗡嗡响。她甚至能想象出他皱着眉、一脸不耐的样子,
额头上也许还沁着油汗——工地上辛苦,她是这么对琳琳说的,爸爸在外地工程上,很累,
我们要体谅他。“体谅”。吴娟无声地咀嚼着这两个字。
她下意识地摩挲着书桌上那本教师资格证,旁边是自考本科汉语言文学的毕业证书封皮,
用了她整整四年的夜晚和周末。她原以为,等到琳琳上高中住校,
她就能有更多时间备考教师编,这个家总能一步步朝着更好的方向去。
这种无法掌控的、下坠的感觉,近来如影随形。她试图用理性的分析压下它——他忙,
压力大,工地环境差,他脾气变坏也情有可原……可女人那点可怜的直觉,
却像藤蔓一样疯长,缠绕得她几乎窒息。太反常了。失联,易怒,
还有那种刻意的、带着表演性质的抱怨和指责,
仿佛急于给她扣上一顶“不贤惠不体贴”的帽子。
她需要一点什么东西来锚定自己慌乱的心神,哪怕只是虚幻的依托。目光扫过书架,
落在那本边缘有些卷曲的《周易浅释》上。早年兴趣所致,翻过几遍,说深信不疑谈不上,
但此刻,它像一根飘在水面的稻草。铜钱冰凉的触感让她打了个激灵。合掌,闭眼,
心绪芜杂,那个不敢深想的猜测是唯一的祈问。铜钱掷落,嗒、嗒、嗒,
声音在过分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。一次,两次,六次。爻象渐成。泽风大过。
她的心猛地一沉。泽灭木,舟沉于水,这是大过之象。
指尖微颤地划过解释的文字——“栋桡,凶”。房屋的栋梁弯曲了,要塌了。
九二:“枯杨生稊,老夫得其女妻”。九五:“枯杨生华,老妇得其士夫”。
爻辞直白得像一记耳光,狠狠扇在她脸上。中年男女,悖逆常理,枯木妄图逢春。这卦象,
并非简单的倦怠或争吵,而是彻底的背叛,是根基的腐烂。甚至…变爻隐隐牵扯子息?
她猛地吸了一口气,想把这无稽的推断甩出脑子。封建迷信!她一个正在备考教师编的人,
怎么能信这个? 可那股味道……那股仿佛从婚姻内核里散发出的、无可挽回的腐败气味,
似乎透过这冰冷的卦象,更加清晰地钻进她的鼻腔,让她一阵阵反胃。
她瘫坐在椅子上 就在这死一样的寂静里,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下。不是一个她期待的姓名,
而是一个陌生的头像,一条好友申请验证消息,简单直接,
甚至带着点不容置疑的探询: “通过一下,有事问你。”没有署名,没有来源。
吴娟的心跳骤然停了一拍,盯着那条消息,仿佛那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,
正在无声地吞噬过来。卦象的凶兆还摊在桌上,铜钱泛着幽冷的光。窗外,
天色彻底暗沉下去。那具名为婚姻的躯壳,仿佛就在这一刻,在她鼻尖下,
正式散发出了第一缕难以忽视的、令人作呕的尸臭。2 破碎那股尸臭,
在第二天就变得具体而锐利,像一根冰冷的针,刺破了吴娟强自维持的平静。
起因是琳琳的升学。分数线预估出来了,琳琳的成绩在理想中的那所省重点的边缘徘徊,
险得像走钢丝。班主任私下联系吴娟,隐晦地提点:“……往年都有这种情况,差个一两分,
如果确实优秀,家里也有那个……嗯,支持学校建设的意愿,也不是完全没机会。
就是这笔‘建设费’,得提前准备好,十万,一次性。机会稍纵即逝,分数线一划定,
多少钱都买不来了。”十万。这个数字砸下来,吴娟心头一沉。家里的积蓄不是没有,
但大多在周涛手里攥着,他说工地周转、应酬都需要钱,自己的证书才刚考下来,
家里收入确实主要靠他。她每月拿到的生活费,刚够覆盖她和琳琳的日常,精打细算,
也存不下几个子儿。她必须跟周涛商量。电话打过去,依旧是漫长的忙音。
她发了条长长的微信,语气尽量平和,陈述了事情的紧迫性和那十万块的关键,
末尾加上一句:“孩子的未来是大事,你那边要是紧张,我看看想想办法找同学借,
但大头还得咱们来。”信息发出去,如同泥牛入海。她不知道,
这条满载着一个母亲焦灼期望的信息,
此刻正和无数条她之前发的、关于生活费、关于家里电器维修、关于女儿成绩的消息一起,
躺在另一个女人的手机屏幕上。城市的另一端,
一个打扮得与年龄略显违和、眉眼间带着精明和焦躁的女人,正飞快地滑动着屏幕,
嘴角撇着冷笑。她叫马莉,离异,带着两个孩子一儿一女,也都在上初中阶段。
周涛对她说的版本是:前妻狠毒,卷走了他千万家产跟野男人跑了,
留他一个孤家寡人辛苦打拼还债,遇见了她,才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温暖。
他给她看过一张模糊的法院判决书照片,
和一张他站在某豪华楼盘样板间里意气风发的旧照工地办公室照片。马莉信了,或者说,
她愿意信。一个自称曾经千万身家、如今落魄但依旧有门路、对她孩子还不错的男人,
是她能抓住的最好的浮木。她急着给孩子们找后路,逼着周涛多掏钱报各种昂贵的补习班,
换租更大的房子。周涛的工资,在她看来,理所应当该更多地流向她和她的孩子。
吴娟那条要十万块的信息,像点燃了炸药桶。 “十万?给她那个丫头片子买分?
”马莉的声音尖利起来,把手机几乎戳到刚进门的周涛脸上,“周涛!你跟我说你没钱!
给我儿子报个三千的编程班你推三阻四,那边一开口就是十万!你把我当傻子糊弄是吧?
你到底离没离婚?!这钱你要是敢给,我立马去你工地!”周涛一脸疲惫与烦躁,
工地上是真忙,应付马莉更是耗神。他一把推开手机,语气冲得很:“你闹什么闹!
那是考高中!正事!我能不管吗?” “正事?我儿子上学就不是正事?周涛,我告诉你,
这钱,没门!你敢动一分,我跟你没完!”马莉扑上来撕扯他的衣服,“你说!
你是不是根本没离婚?你是不是还跟她过日子呢?你这个骗子!”周涛被闹得头昏脑涨,
心底那点因为欺骗而生出的愧疚,早已被无穷尽的索取和吵闹磨光,只剩下厌烦。
他猛地甩开她,低吼道:“钱钱钱!就知道钱!我跟你说过多少遍,
我的钱都被那女人掏空了!现在挣的这点够干什么?琳琳上学那是她的命!有本事就考上去,
没本事就认命!我能有什么办法?!”这话,他几乎是原封不动地,
在第二天吴娟终于打通他电话时,吼给了吴娟听。语气里的不耐和冰冷,将吴娟彻底冻僵。
“十万?我去哪偷十万?你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?分数线差几分?那就是她的命!
考不上就上差一点的,死不了人!别天天拿这些破事来烦我!我够累了!”电话被粗暴挂断。
吴娟捏着手机,站在炎热的夏日傍晚,却觉得浑身血液都凉透了。破事?女儿的前途是破事?
命?他轻飘飘地就判了女儿“认命”?而一个归属地陌生的号码发来的短信。
在周涛吼完那通电话后不到半小时,突兀地闯了进来。
语气是毫不掩饰的嘲弄和恶意: “我说,这位前妻姐姐,
你都跟人跑了把周涛坑那么惨了,怎么还有脸伸手要十万?给你那拖油瓶女儿买分?
周涛现在赚的都是血汗钱,要养也是养他现在的家!识相点就别再缠着他要钱了,
给自己留点脸吧!”吴娟盯着那几行字,看了足足一分钟。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,
烫得她视线模糊。前妻?跟人跑了?拖油瓶?现在的家? 世界在她眼前碎裂、重组,
露出狰狞丑陋的内核。卦象上那根弯曲的栋梁,轰然倒塌,扬起漫天腐朽的尘埃。
她手指颤抖着,回拨周涛的电话——已关机。 她打给他常联系的工友,对方支支吾吾,
只说:“嫂子,周哥这两天好像是不在工地,可能出去办事了吧?手机……可能没电了?
” 她咬牙,报警人口走失。警方反馈需要直系亲属且失联超过48小时,建议再联系家人。
她最终把电话打给了周涛在老家的姐姐。大姑姐听完,沉默了一会,
语气有些古怪:“小娟啊,你别急,兴许手机真丢了。
我昨天……昨天下午还看他发朋友圈呢,好像在外面吃饭,看着挺高兴的……可能忙,
没顾上跟你说吧?我再帮你问问。”昨天下午?朋友圈?
吴娟猛地翻开周涛的朋友圈——对她,只有一条冷冰冰的横线。 今天,是七夕。
所有的线索,所有的谎言,所有冰冷的言语和那条恶毒的短信,在这一刻串联起来,
指向一个鲜血淋漓、恶臭扑鼻的真相。他不是在忙,不是手机丢了。
他是在用他们女儿的前途钱,用他们这个家的积蓄,在七夕节,陪另一个女人,
和别人的孩子,过节。吴娟缓缓滑坐在冰凉的地板上,窗外传来邻居家炒菜的香气,
电视里欢快的广告声,整个世界依旧喧嚣而正常。只有她的世界,万籁俱寂,
只剩下那腐烂的恶臭,无处不在,钻心蚀骨。她知道了。她终于,必须要面对了。
3 三观尽毁吴娟就那样坐着,很久,很久。窗外霓虹闪烁,映照着她一张失了血色的脸。
脑子里是空的,又像是被无数嘈杂尖锐的噪音塞满。那条恶毒的短信,
周涛冰冷的“认命”论,大姑姐言语间的闪烁,还有……七夕节。
这些碎片在她脑海里疯狂碰撞、旋转,最终拼凑出一张巨大而丑陋的真相之网,
将她死死缠裹,勒得她喘不过气。她从未想过。这个词跳出来,带着一种天崩地裂的荒谬感,
狠狠嘲笑着她过去十五年所坚信的一切。结婚时,她图他什么?图他农村老家一贫如洗?
图他母亲早逝、性格里那份她曾误读为“早熟稳重”的孤僻阴郁?她自己的父亲也去得早,
她是家里老三,上面两个哥哥,母亲身体不好,她在父亲去世后几乎和母亲相依为命,
以为和周涛是同病相怜,是风雨里两只湿透了羽毛的雀鸟,能互相依偎着取暖,
总能搭建一个遮风避雨的小窝。没要彩礼,没置办三金,甚至婚礼都简单得近乎寒酸。
姐姐们私下说她傻,她只是笑,觉得她们世俗。她那时笃信,真心比黄金珍贵,
共同的苦难经历是最牢靠的婚姻基石。她看中的是他沉默肯干,
是她自以为能触摸到的、他内心深处那份与她相似的、对完整家庭的渴望。廉耻,诚信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