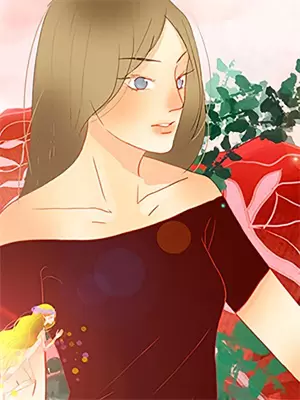我家有个祖传的肉苁蓉洞,只传女,不传男。
女人进去后,洞内总会传来奇怪的声响,不是哭不是笑,倒像被什么缠得发颤的低吟。
提起洞内的景象,她们总咬着发红的指尖,眼尾泛着潮意。
一夜之间她们容光焕发,连走路都带着股松快的软劲。
我总趁她们不注意,往洞口探着看。
黑黢黢的洞里飘着股异香,勾得人心里发痒。
可她们总拍我的手,“小丫头片子急什么,等你成年了,这个洞都是你的!”
终于,熬到了我十八岁这天… …
天刚蒙蒙亮,洞门口的老皂角树就被红绸缠得满满当当。
我穿着娘连夜缝的新布衫站在石阶上,她一只手攥着我,另一只手里捧着个描金漆盒,盒角的金粉已经掉了大半。
“别慌,等会儿跟着四婆的话做。”
吉时一到,鞭炮炸出一串火星。
四婆被两个媳妇扶着,颤巍巍揭开了漆盒——里头躺着一把铜钥匙。
“这钥匙,如今该传你了。”四婆的牙豁了个口,说话漏风。
我刚接过钥匙,洞门那边就飘来股怪味。
像灶台上没冲净的洗洁精,又裹着点甜腥。
我盯着那扇老木门,门板上的裂纹里嵌着层黑泥,不知积了多少年。
“该开门了。”娘推了我一把。
我刚把钥匙往门眼送,不远处一道声音传来。
“等一下!她不能继承这个洞!”
众人齐齐转身望向声音的来源。
只见那人站在皂角树后头,穿的布衫跟我身上这件一式一样,连袖口磨出的毛边都分毫不差。
雾气散了些,看清她脸的一瞬间,我僵在了原地。
她的左眉梢有颗小米粒似的痣,眼下像是熬夜留下了些青黑,连嘴角那点天生的小豁口,都和我一模一样!
“妹妹。”她先开了口,声音比我的脆些,“我是你的双胞胎姐姐,比你早生十分钟。按照族里的规矩,这个肉苁蓉洞,该由我来继承。”
我攥着钥匙的手猛地收紧,娘从没说过我有姐姐,连村里最碎嘴的二婶,都没提过我家当年生的是双胎。
“娘?”我转头去看娘,她却错开眼,望着皂角树的方向,嘴唇动了动,没说出话,只轻轻点了下头。
周围的议论声突然低了,所有人都看着那个自称姐姐的人,眼神里没多少惊讶,倒像早就等着这刻。
她朝我走过来,指尖擦过我手背,拿走钥匙时,我摸到她掌心也有颗跟我位置相同的薄茧——那是常年帮娘捶衣裳磨出来的。
她站到洞门前,背影像极了我自己。
铜钥匙插进木眼的瞬间,发出“咔嗒”一声轻响,像被什么东西严丝合缝的含住了。
洞门,开了… …